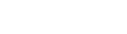九广网讯(文/游会雄)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农村实行“包产到户”后,我们那里除了种植早晚稻、红薯和冬小麦等粮食作物外,还广种油菜、大豆、芝麻和花生等经济作物。我们上学读书主要是靠卖菜籽、大豆和稻谷的收入。因此,凡周末假期,我们便是家中父母的好帮手!
那时,我刚入初中,还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。学校似乎很“人性化”,大概多数老师也是吃“农业粮”的吧,都要回家帮忙农事。每年春、秋两季,学校都会放大约一周左右的“农忙假”。暑假二个月,我们正可以帮得上家中的生产劳作。既能得到好的收成,增加家庭收入;我们也经受了一份不曾有过的人生磨砺。回想那时的假期生活,真的依然感慨万千……
七月初,小暑节气临近,气温逐渐攀高。播种在山地、坡坎上的大豆,开始落叶成熟,此时我们已放暑假了。“农人的孩子早当家。”刚放假,记得先是母亲带我们到秧田拔稗草,加施些化肥,来个适应性“热身”吧!起始,我们不听父母要“戴草帽,穿长衣”的劝告。光着头,穿着短袖,在日头下干些轻活。一两天下来,竟被晒得面红耳赤,手臂火辣辣的,真切地感受到日头的厉害了。
大约三四天后,村上村下,田间地头,开始弥漫着忙碌的气氛。头天晚上,父亲备好了三四把镰刀和两三担高脚篼。母亲对我们说:“明天早上,你们俩兄弟去葫芦丘山割豆,别酣(睡)得太晏(迟)了哦!”我们默然不做声,晓得劳累的日子要来了。
我们十三四岁的孩子,正瞌困重,早上好睡。待到醒来,慌了神,已是日上三竿了。我们匆忙地赶到豆地。母亲躬背弯腰在割着豆,已经割了好一大块地,衣袖和裤腿都被露水湿透了。有时,我们梦醒后竟忘了带镰刀等农具,慵懒地空着手去割豆。“春争日,夏抢时。”若要返家去拿的话,更是耽误了工夫。这几乎要把母亲气个半死。母亲只好问问周遭割豆的人家有没有多余的备用镰刀。正好有人割完了豆地(有的四五点钟起床,天刚亮就下地干活)。我们立刻借了过来,这样才算缓解了母亲心头的火气。
在父母的辛苦劳作后,山地里的大豆长得真好,豆杆粗,结荚多。硬实的豆荚尖刺得手痛,不多久就会冒出小血眼。不巧的是在未落尽的青黄豆叶上,有种浑身是细针状带有剧毒的黄青虫,我们乡下叫“痒辣得"。若不小心让手碰到它身上,那就痒痛要命得难受。母亲也没法治它,只是告诉我们割豆时要细心,别碰着它为好。可是,再细心也难免不碰到,最多是万一不小心碰到就赶紧缩手或者是后来皮肤有了抵抗力,疼痛也会好好多。
一早晨加半上午下来(早饭吃得晚,有时爷奶送点心),大约要在十点,二三亩大的豆地才能割完。浑身浸透了汗水和露水,裤袖管上结满了糯米虫般的草籽,这副形象仿佛是战场上打仗归来的邋遢士兵。割下的豆堆,每人先装满高脚篼,挑一担回家,剩下的暂放在豆地里晒一晒,待晒干一些水分,吃完早饭再来用高脚篼担回家,这就完成半天的任务了。
母亲回得家来,上午将豆箕匀铺在门口道场上晒。中午就开始用梿枷(一种脱粒用的农具)打场脱豆。连同邻家的这些农活,真有那种宋代诗人范成大在《四时田园杂兴》中形容的“笑歌声里轻雷动,一夜连枷响到明”的动人场景。
下午三点多了,太阳的热度依然不减。我们穿着厚衣,戴上草帽,挑着高脚篼。篼里放上镰刀和一大瓶水,向另一块豆地进发。这块豆地有一亩三,地势低洼,旁边有水沟,土壤较潮湿,极易长草。母亲说:“这块地的草好难锄。地湿,草不易锄死。前期因雨水较多,草长得比豆苗还快。”怪不得远远望去,豆杆都藏在草地里,难见踪影。我们只好在草地里扒着割豆。因地肥,不用说豆好,草也好。我们顶着燠热的高温,地里没有一丝儿风,任凭日晒地蒸,浑身汗流如注,衣背湿透。望着偌大的豆地,还只割到一大半,体力已消蚀得差不多了。心想:汗水流干,也不知能否割完。我实在热得受不了,索性跑到地坎上歇息,“咕噜咕噜”地喝着带来的冷开水,似乎这就是莫大的享受。不像现在,坐在家里开着电扇或空调不做么事,还一个劲地喊“热”啊!
太阳好不容易偏西了,热度消减了很多,人也稍稍有些舒适。可被汗水浸透的身上,汗渍的馊味惹来了虻蝇。只要你俯身低头割豆,虻蝇就像轰炸机一样“嗡”的蹿下来,逐着汗味,盯着你的皮肉咬,难受得很。太阳快西沉了,只剩下一个红彤彤的大圆盘。我们提速将豆地割完,然后将大豆装篼担回家。父母已挑回二三担了,各自只剩下最后一担。我匆促地装完高脚篼,而装篼是个技术活,因经验不足,没塞结实,挑着挑着,在半路竟爆篼了,实在无奈之极。这时,天色已然暗了下来,急得哭喊也没有用,只有耐心重装再挑。幸好父亲及时赶来,帮着挑了回去。不然,我真不知要捱到何时。
回到家,撂下镰刀,脱掉湿衣,拿着毛巾,赶紧冲到门口的大堰塘去洗澡。月亮从东山升起来了,月色很好。